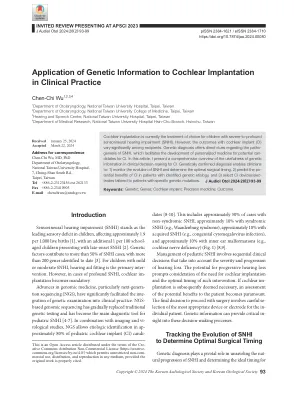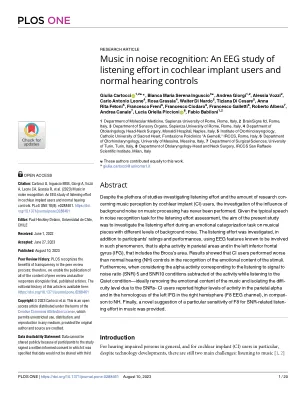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一种新型药物输送:纳米耳蜗
Dimitrious Papahadjoupoulos 博士及其团队发现,蜗壳是由带负电荷的磷脂酰丝氨酸与钙相互作用形成的沉淀物。它们用于通过递送肽和抗原来提供疫苗。在纳米蜗壳(一种新型药物递送载体)中,目标药物分子被包裹在多层结构中,包括螺旋形薄片内的固体脂质双层。这种方法使用药物的蜗壳化来克服诸如溶解度差、渗透性和口服生物利用度差等问题。它们保护分子免受 pH、温度和酶等恶劣环境条件的影响。由于其表面和结构上同时具有亲水性和亲脂性形式,因此它可以同时包含亲水性和亲脂性药物分子。药物分子的包封负载能力由蜗壳的物理结构决定,而包封程序决定了形成的复合物的粒度。它可用于口服和全身给药生物活性物质,包括药物、DNA、蛋白质、肽和疫苗抗原。这种方法既可用于全身治疗,也可用于口服治疗,最终可能发展成为药物输送系统。这些因素将鼓励研究人员研究这一新兴的药物输送技术领域。有许多方法可以创建纳米耳蜗,然后可以使用它们来为各种应用施用不同的活性化合物。本文讨论了纳米耳蜗的组成和结构以及这些化合物的给药机制、制造技术、评估、用途和局限性。
植入人工耳蜗的儿童的跨模态可塑性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大脑会响应环境刺激而发生实质性的组织。在寂静的世界中,大脑可能通过 (i) 从听觉皮层招募资源和 (ii) 使视觉皮层更有效率来促进视觉。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何时发生以及它们的适应性如何,植入人工耳蜗的儿童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检查了 7-18 岁的儿童:50 名儿童植入了人工耳蜗,语言能力发育迟缓或与年龄相符,25 名儿童的听力和语言能力正常。高密度脑电图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用于评估皮层对低级视觉任务的反应。有证据表明,语言发育迟缓的植入儿童存在“视觉皮层反应较弱”和“听觉联想区同步性较差或抑制性较差”的情况,这表明跨模态重组可能具有不良适应性,并不一定会增强主导视觉。
将遗传信息应用于人工耳蜗...
感觉性听力障碍(SNHI)是儿童的领先感官缺陷,影响了每1000名活出生的大约1.9个[1],每100名年龄的儿童又有1个较晚的SNHI [2]。遗传因素造成了超过50%的SNHI病例,迄今为止有200多个基因[3]。对于患有轻度或中度SNHI的儿童,助听器配件是主要的相互作用。但是,如果SNHI深刻,人工耳蜗变得强制性。基因组医学的进步,尤其是下一代测序(NGS),已经显着促进了遗传检查对临床实践的全面。ngs的基因组测序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基因检测,并已成为小儿SNHI的主要诊断工具[4-7]。与成像和Vi-Rogogation研究结合使用,NGS允许在大约80%的小儿耳蜗(CI)Canti-
人工耳蜗期间的机器人援助
人工耳蜗(CI)通过提供一种绕过正常听力以直接刺激听觉神经的方法来彻底改变了严重至深刻的感觉听力丧失患者的治疗。在现场进一步的进步是引入“听力保存”手术,因此,仔细插入了CI电极阵列(EA),以避免对耳蜗的细腻解剖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保留内耳的残留功能使患者可以从CI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并将CI电刺激与声学听力结合起来,提供改善的术后言语,听力和生活质量。然而,在当前手动插入EA的植入手术范式下,无法可靠地免除耳蜗。机器人辅助EA插入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克服基本的人动力学局限性,可防止在实现稳定和缓慢的EA插入方面的一致性。本综述首先描述了EA插入速度与应变后力和压力的产生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这些对等方内力可能损害耳蜗并导致术后恶化的各种机制。将手动插入技术的约束与机器人辅助方法进行了比较,然后概述了机器人辅助EA插入的当前和未来状态。
人工耳蜗 - 新加坡
2.3。目前,BCHIS和可穿戴的BCD已针对SSD儿童提供补贴。两种治疗方法都可能在功能增益,听力 - QOL和患者满意度方面提供改善,但是,BCHIS和可穿戴的BCD不会恢复双耳听力,并且在聋哑耳朵中长期缺乏刺激可能会影响大脑发育。2.4。CI系统分别由位于皮肤下和人工耳蜗内的耳朵和内部成分(接收器,电极)后面的外部组件(声音处理器,发射器)组成。声音被捕获,并由声音处理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过发射器发送到接收器。接收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电能以刺激耳蜗神经。然后大脑将刺激解释为声音。由于其作用机理,CI系统是在有耳蜗神经缺乏症的患者中禁忌的。假设CI可以直接刺激非听力耳朵来恢复双耳听力。CI可能会从四年以下儿童中逆转异常皮质组织,因为年轻时的神经可塑性更高。在长期听力剥夺或耳蜗神经缺乏症患者中,BCHI或可穿戴的BCD是首选。技术的总体好处
噪声识别中的音乐:人工耳蜗植入者和正常听力对照者的听力努力的脑电图研究
尽管有大量研究调查聆听努力程度以及有关人工耳蜗 (CI) 用户音乐感知的研究,但是从未有人研究过背景噪音对音乐处理的影响。鉴于聆听努力程度评估的典型噪声中语音识别任务,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在不同背景噪音水平的音乐作品上进行情绪分类任务时的聆听努力程度。除了参与者的评分和表现之外,还使用已知与这种现象有关的 EEG 特征来调查聆听努力程度,即顶叶区域和左侧下额叶 (IFG)(包括布罗卡区)的 alpha 活动。结果表明,CI 用户在识别刺激的情绪内容方面的表现差于听力正常 (NH) 对照组。此外,当考虑对应于听信噪比 (SNR) 5 和 SNR10 条件的 alpha 活动时,减去听安静条件下的活动(理想情况下,去除音乐的情感内容并隔离由于 SNR 而导致的难度级别),CI 用户报告的顶叶 alpha 和右半球左 IFG 同源体(F8 EEG 通道)的活动水平高于 NH。最后,提出了 F8 对与 SNR 相关的音乐聆听努力具有特殊敏感性的新建议。
基因治疗:耳蜗毛细胞再生的新兴疗法
神经性听力损失通常是由于外界刺激或遗传因素导致耳蜗毛细胞受损,无法将声机械能转换成神经冲动所致。成年哺乳动物耳蜗毛细胞不能自行再生,因此这种类型的耳聋通常被认为是不可逆的。对毛细胞分化发育机制的研究表明,耳蜗内非感觉细胞通过特定基因(如Atoh1)的过表达获得分化为毛细胞的能力,使毛细胞再生成为可能。基因治疗是通过体外筛选和编辑靶基因,将外源基因片段导入靶细胞,改变基因的表达,启动靶细胞相应的分化发育程序。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与耳蜗毛细胞生长发育相关的基因,并概述了基因治疗方法在毛细胞再生领域的应用。最后讨论了当前治疗方法的局限性,以促进该疗法在临床环境中的尽早实施。
脑干神经元的时间超精油改变双耳听觉加工的空间敏感性用耳蜗植入物
在复杂环境中定位声源的能力对于通信和导航至关重要。空间听证会主要依赖于两只耳朵之间声音到达时间的差异的比较,即播出时间差异(ITD)。听力障碍对声音本地化非常有害。尽管人工耳蜗(CIS)成功地恢复了许多关键的听力能力,但通过ITD检测与双边顺式合理的定位仍然很差。根本原因尚不清楚。神经元,ITD敏感性是通过专门的脑干神经元进行的两只耳朵的兴奋性和抑制输入之间的巧合检测而产生的。由于在CI刺激过程中缺乏电生理学脑干记录,目前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双耳比较神经元引起的,或者已经在输入水平上引起。在这里,我们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比较CI听力动物模型中电气和声学刺激之间的响应特征。在Gerbils中进行细胞外单神经元记录,我们发现在电脉冲刺激期间,兴奋性和抑制性脑干输入对双耳比较神经元的兴奋性和抑制性脑干输入中等高度渗透性。这一发现确定,双耳处理阶段必须应对CI刺激期间的输入统计量的高度变化。为了估计这些影响对ITD灵敏度的后果,我们使用了听觉脑干的计算模型。调整模型参数以使其响应特性与我们在任何一种刺激类型期间的生理数据相匹配时,该模型预测,即使对于超专有输入,也可以保持对电脉冲的敏感性。然而,与声学相比,该模型在电刺激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改变的空间敏感性:
鸽子耳蜗内铁细胞器的量子磁成像
尽管缺乏对潜在生物物理机制的明确了解,但鸽子感知地磁场的能力已得到最终证实。鸽子耳蜗中的准球形铁细胞器以前被称为“角质体”,由于其位置和铁成分,与磁感应具有潜在相关性;然而,目前有关这些结构的磁化率的数据有限。这里应用量子磁成像技术来表征单个铁角质体的原位磁性。从角质体发出的杂散磁场被映射并与详细的分析模型进行比较,以提供单个粒子的磁化率估计值。图像显示单个角质体内存在超顺磁性和亚铁磁性域,磁化率在 0.029 到 0.22 范围内。这些结果为了解角质体难以捉摸的生理作用提供了见解。测量的磁化率与基于扭矩的磁感应模型不一致,将铁储存和静纤毛稳定作为两个主要的假定角质体功能。这项研究确立了量子磁成像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可以补充现有的一系列用于筛选潜在磁性粒子磁受体候选物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