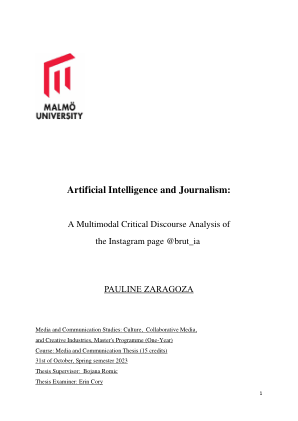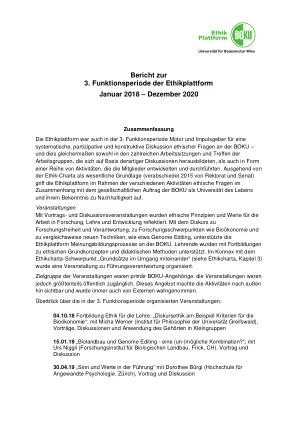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美丽的叉子灯塔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 2:15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是智慧、知识和理解终极现实的唯一确凿来源。它是真理的源泉和实用原则的金矿,等待着解放和丰富追求真理和财富的人。保罗的教导“要殷勤作工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基督徒用作学习上帝之道的指示。健康、平衡生活的唯一方法是“按着正意分解”上帝的话语。正确运用上帝之道的能力是勤奋学习的结果。诗篇 119:11 进一步敦促人们记住上帝的话语,将其作为抵制罪恶的强大威慑。记住圣经可以立即获得上帝的话语作为宝剑,随时准备作见证并在属灵战争中发挥作用。当我们继续将上帝的话语灌注到我们心中时,就让上帝之道“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心里”(歌罗西书 3:16),今天以及每一天!
对人工智能偶然形成的批判性视角
本章从批判性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作为当代社会中一个关键的社会技术制度的偶然形成。它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仅是功能性技术发展和改进的产物,而且同样取决于经济、政治和话语驱动因素。它以 STS 和批判性算法研究为基础,表明技术发展始终取决于并源于沿着多条科学轨迹的转变以及多个参与者和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我们对人工智能及其认识论的概念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它将注意力引向不同的问题:远离事后检测影响和偏见,转向以人工智能如何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技术实体为中心的视角。我们从三个关键领域阐述了这一过程:技术研究、媒体话语和监管治理。关键词(6 个关键词):人工智能;STS;形成;认识论;话语;治理。
迈向一项一次性数据驱动指南
虽然最近在代理[9]和机器人文献[24]中进行手势合成的工作已将手势视为共同语音,因此依赖于口头话语,我们提供了表明手势可以利用模型上下文的证据(即导航任务),不仅取决于口头话语。这种效果在含糊不清的口头话语中尤为明显。将这种依赖性解耦可能会使未来的系统能够综合澄清手势,这些手势阐明了模棱两可的口头话语,同时使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手势的语义。我们从这个领域中的经验中汇集了证据,使我们能够首次看到需要开发哪种端到端的关注模型,以合成一声互动的手势,同时仍然可以保留用户的结果并允许机器人模棱两可。我们在“基本方向手势计划”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该指示指的是人类将来必须遵循的行动。
人工智能与新闻:
社交媒体平台上数字新闻的兴起正日益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对于年轻受众而言。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所制作的数字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也对所传达的话语提出了质疑。以法国 Instagram 页面 @brut_ia 为例,该页面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闻对象和内容创建工具,通过改编自 Fairclough 模型的多模态批判性话语分析,分析了该账户的制作和话语的见解及其对人工智能和新闻关系的重新构建。通过使用数字新闻逻辑和计算创新以及视觉新闻话语和新闻价值观,结果突出了传统和新颖新闻实践的混合,以及受 Instagram 平台逻辑影响的以积极和娱乐为主的人工智能话语。总体而言,本研究突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账号制作和讨论如何影响新闻传播、呈现和推广,但也提出了一些局限性。
报告道德平台的第三阶段一月...
话语可能有助于澄清重要问题,例如生物经济。因此,话语伦理的概念被选为2018年秋季进一步培训“教学伦理”的重点主题。例如,生物量的使用应有什么优先级,例如:食品或饲料,基于生物的行业或能源产生?可以通过广泛的论述来实现解决这种竞争情况的共识。博士教授格里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迈克·沃纳(Micha Werner)在演讲中介绍了话语伦理的概念。 在练习的培训日,培训日的下午单位,博士托马斯·林丹塔尔(Thomas Lindenthal),全球变革与可持续性中心,伦理平台的成员。 他在2中概述了道德平台。 功能时期创建了纸质“生物经济的目标和标准”,概述了这项未来技术的潜力和挑战。 使用本文,参与者尝试了两个小组,据此,可以在讨论中实施话语伦理的概念以及如何将其整合到教学中。博士教授格里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迈克·沃纳(Micha Werner)在演讲中介绍了话语伦理的概念。在练习的培训日,培训日的下午单位,博士托马斯·林丹塔尔(Thomas Lindenthal),全球变革与可持续性中心,伦理平台的成员。他在2中概述了道德平台。功能时期创建了纸质“生物经济的目标和标准”,概述了这项未来技术的潜力和挑战。使用本文,参与者尝试了两个小组,据此,可以在讨论中实施话语伦理的概念以及如何将其整合到教学中。
北京“乡村振兴”战略国际传播话语分析
摘要:本文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为数据,对“乡村振兴”战略内容进行话语建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有助于构建特定的话语生态,在国际上发出声音。报告通过介绍北京深入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信息,立足本土,呈现首都鲜明的经济形象,展现政府务实的作风和以人为本的担当。研究有助于了解政治战略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建构特征,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实施及其鲜明的成就,从而更好地通过首都北京这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了解中国。
通过定位交流互动
紧急沟通领域调查了从事需要交流的合作任务的自主代理之间共同的语言惯例的出现。通过自组织产生的惯例更加稳健,灵活和适应性,并且消除了手工制作协议的需求。 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研究了人造代理如何在基于参考的任务中共同建设这种语言结构的惯例。 使用语言游戏实验范式解决了此问题,该范式旨在模拟人类语言出现和演变的基础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贡献引入了在紧急环境中针对语言游戏范式的新方法。 使用该方法,代理可以通过自我组织建立一种新兴的语言,使他们能够使用单词话语来指代环境中的任意实体。 第一次,该方法直接适用于任何描述实体连续值特征的数据集。 我的研究中的下一阶段是通过语法结构的出现从单词话语转变为多词的话语。通过自组织产生的惯例更加稳健,灵活和适应性,并且消除了手工制作协议的需求。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研究了人造代理如何在基于参考的任务中共同建设这种语言结构的惯例。使用语言游戏实验范式解决了此问题,该范式旨在模拟人类语言出现和演变的基础过程。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贡献引入了在紧急环境中针对语言游戏范式的新方法。使用该方法,代理可以通过自我组织建立一种新兴的语言,使他们能够使用单词话语来指代环境中的任意实体。第一次,该方法直接适用于任何描述实体连续值特征的数据集。我的研究中的下一阶段是通过语法结构的出现从单词话语转变为多词的话语。
正交表示用于估计因果量的学习
生成的AI在创意和艺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立足点。在这种情况下,创意工作的概念受到源自技术利益相关者和主流媒体的话语的影响。围绕创造力和艺术作品的叙事的框架不仅反映了对文化的特殊愿景,而且还积极地促进了它的构成。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在线媒体,并分析了AI对他们传达的创意工作的影响的主要叙述。我们发现,该话语促进了通过人工劳动实现其物质实现的创造力。通过自动化来实现该思想与其物质条件的分离,这是评估为生产时间减少生产时间的驱动力。以及在执行创作过程中通常需要的技能被视为使创造力民主化的一种手段。这种话语倾向于对应于主要的技术实证主义愿景,并主张对创造性经济和文化的权力。
道德政策中的协商危害:以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为例
将一项政策视为有害会导致对其道德谴责。然而,这种有害性可以通过建立在可用、可访问和相关的话语之上来构建和协商,从而导致不同的道德立场。本研究考察了个人在对一项有争议的政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当地称为“tokhang”)进行道德推理时如何构建和协商危害。我们进行了主题分析,关注话语,分析了对 12 名菲律宾年轻人的采访,以二元道德理论为起点,理解危害的构建。关于“tokhang”的推理表明,作为道德立场基础的故意行为者和脆弱受害者的不同构造。对禁毒战争的道德谴责强调了受害者的脆弱性以及政府和警察作为行为者的故意性。另一方面,该政策的道德辩护将禁毒战争受害者构建为行为者和有罪者,将警察构建为潜在的脆弱受害者,他们按照协议为自己辩护,而流氓行为者则独立于政策行事。当伤害的因果关系不明确时,立场模糊也是可能的。这些建构和协商建立在城市青年社会政治背景下更广泛的话语之上,个人背景和特征导致某些话语的可及性和相关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立场存在差异。
Shineha Ryuma,大阪大学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副主席,国际可持续发展科学与技术会议2024小组委员会,日本科学委员会,日本科学委员会,日本青年学院副主席
关于灾难后的媒体话语,结构性问题和社会脆弱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