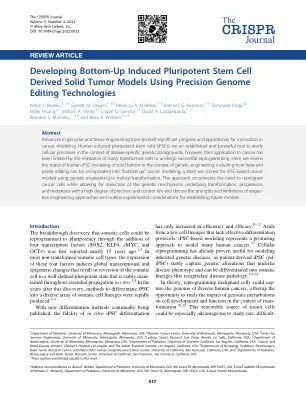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人工智能(AI)或增强...
但是,自1950年代以来,AI一直在开发。Alan Turing介绍了1950年能够思考的机器的概念。[7]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被广泛称为AI的父亲,于1956年创造了这个词。[8] AI是指使用计算机模仿人类智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8]鉴于人脑,神经系统系统和批判性思维过程的复杂性,AI在技术上在多个层面上都具有挑战性。将人类认知功能(例如逻辑,推理,感知,关联,计划,预测,自然语言处理和运动控制)纳入AI技术是非常复杂的。更具挑战性,因为医疗AI在错误成本方面是不可原谅的,但此处却可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和机会。因此,毫不奇怪的是,AI和Big-Data分析在医学方面已变得无处不在,并且正在改变多个学科的医疗保健,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
在完整的两部分图上计数量子
量子计数是一种关键量子算法,旨在确定数据库中标记元素的数量。该算法基于量子相估计算法,并使用Grover算法的进化算子,因为其非平凡特征值取决于标记元素的数量。由于Grover的算法可以看作是在完整图上的量子步行,因此扩展量子计数的自然方法是在不完整的图上使用基于量子 - 步行的搜索的进化运算符,而不是Grover的运算符。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分析具有任意数量的标记顶点的完整两分图上的量子步行来探讨此扩展。我们表明,进化运算符的某些特征值取决于标记的顶点的数量,并且使用此事实,我们表明量子相估计可用于获得标记的顶点的数量。与我们的算法与原始量子计数算法紧密相位的两分图中标记顶点数量的时间复杂性。
使用精确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自下而上的多能干细胞衍生的实体瘤模型
基因组和组织工程的抽象进步刺激了癌症建模创新的显着进步和机会。人类诱导的多能干细胞(IPSC)是在特定于疾病的遗传背景下研究细胞过程的已建立且强大的工具;然而,它们在癌症上的应用受到许多转化细胞对成功重编程的阻力的限制。在这里,我们在基因工程的背景下回顾了实体瘤的人IPSC建模的状态,包括如何将基础和主要编辑纳入“自下而上”的癌症建模中,这是我们使用基因工程来诱导转化的基于IPSC的癌症模型创造的术语。这种方法规定了对癌细胞进行重编程的需求,同时允许解剖具有高度的精度和对照的转化,进展和转移的遗传机制。我们还讨论了建立未来模型的重大工程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
人工智能在兽医学中的应用综述
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学院授课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 (AI) 一词 (Bini, 2018)。尽管该术语现已融入日常生活,但对 AI 尚无标准定义 (Samoili 等人, 2020)。AI 的众多定义之一是“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从此类数据中学习并通过灵活适应利用该学习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Kaplan 和 Haenlein, 2019)。目前,AI 在人类医学实践和研究中的融入程度高于在兽医学中的融入程度,但其许多应用(如成像、诊断和健康记录)与兽医学同样相关。例如,人类医学中已经建立了医疗编码基础设施来协助医生并改善临床研究。同样,兽医研究现在正在研究大规模使用电子健康记录来根据自由文本预测诊断
关于机器智能不可能实现的论据
自从“人工智能”这个名词短语被创造出来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够利用技术创造智能。我们从热力学和数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首先,我们定义了什么是可以成为人工智能载体的代理(设备)。然后我们表明,由 Hutter 等人提出的、至今仍被人工智能界接受的“智能”的主流定义太弱,甚至无法捕捉到当我们将智能归因于昆虫时所涉及的内容。然后,我们总结了 Rodney Brooks 提出的非常有用的基本(节肢动物)智能定义,并根据此定义确定了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具备的属性,才能成为智能的载体。最后,我们表明,从创建这种代理所需的学科(即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属性既不能通过隐式或显式的数学设计来实现,也不能通过设置一个人工智能可以自发进化的环境来实现。
针对三种目标化合物的 Azacryptand 结构优化...
串联重复序列,或广义上的卫星序列,是基因组普遍性和功能相关性研究最多的重复序列。卫星序列这一术语于 1961 年诞生,因为在平衡沉降实验中,这些序列分布在主体 DNA 带的上方和下方。 [3] 卫星序列根据其大小可分为:i)微卫星序列或短串联重复序列 (STR),既短(每个模式 2 到 6 bp 长的序列),又丰富(约覆盖我们基因组的 3%),代表性例子是端粒微卫星 d[TTAGGG] n ,重复序列 >10 kb;ii)微卫星序列/模式长约 15 bp,阵列长度高度可变(从 0.5 到 30 kb); iii)卫星(约 200 bp 长的序列/模式)构成了着丝粒和着丝粒周围和亚端粒区域的大部分,其中 α 卫星最为丰富(约占卫星 DNA 的 50% 和所有 DNA 重复的 10%);以及 iv)大卫星(> 1 kb 长的序列/模式)代表大的染色体区域。[4]
注意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 1 的概念最早由赫伯特·西蒙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他将信息过载问题描述为经济问题。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内容(供应)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且可立即获得,注意力成为信息消费的限制因素,这一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见附件 2 1 。虽然可访问信息的供应量持续快速增长——数字数据大约每两年翻一番——但对信息的需求却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稀缺注意力的限制。事实上,总的可用注意力受到可访问信息的人数 2 和一天中固定的小时数以及对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相互冲突的需求的限制。达文波特和贝克(2001)首先将“注意力经济学”定义为一种信息管理方法,将人类注意力视为稀缺商品,并应用经济理论解决各种信息管理问题 3 。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注意力经济”而不是“信息经济”中。
黄色经济
注意力经济 1 的概念最早由赫伯特·西蒙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他将信息过载问题描述为经济问题。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内容(供应)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且可立即获得,注意力成为信息消费的限制因素,这一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见附件 2 1 。虽然可访问信息的供应量持续快速增长——数字数据大约每两年翻一番——但对信息的需求却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稀缺注意力的限制。事实上,总的可用注意力受到可访问信息的人数 2 和一天中固定的小时数以及对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相互冲突的需求的限制。达文波特和贝克(2001)首先将“注意力经济学”定义为一种信息管理方法,将人类注意力视为稀缺商品,并应用经济理论解决各种信息管理问题 3 。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注意力经济”而不是“信息经济”中。
数字孪生 - 奥雅纳
数字孪生正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2003 年,Michael Grieves 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研究中创造了“数字孪生”一词。1 在第 24 页,Grieves 博士阐述了数字孪生在建筑环境中的演变。通用电气、西门子和劳斯莱斯早在该术语诞生几十年前就借助模拟技术设计了转子、涡轮机和发动机。同样,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自 1980 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燃料库的模拟。在 Grieves 创造该术语之前,行业使用的术语多种多样,例如“数字阴影”、“数字化身”和“数字模型”。回顾数字孪生的历史,我们必须在数字模型、模拟和数字孪生之间做出重要区分。数字孪生不是静态模型,而是连接物理系统和数字系统之间的响应系统。在以下段落中,我们提供了行业如何思考和采用数字孪生的示例。
虚拟工程团队:战略与...
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工具革命’的经验来应对代表范式转变的‘通信革命’?”直接的反映是,我们将高估技术、流程自动化和工作流支持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家创造了“技术决定论”一词,表达了这样一种天真的信念:所有问题都是技术性的,技术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Andersen,1995)。虚拟团队合作的核心是沟通,沟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和组织问题。我们希望团队成员即使不在同一地点也能紧密合作,发展社会和职业关系。作者认为,通信技术不会取代社会亲近,这种亲近仍然是建立信任和信心所必需的。社交、面对面的环境。另一方面,通信技术是虚拟团队合作的关键推动因素。采取跨学科方法势在必行,同时不能低估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