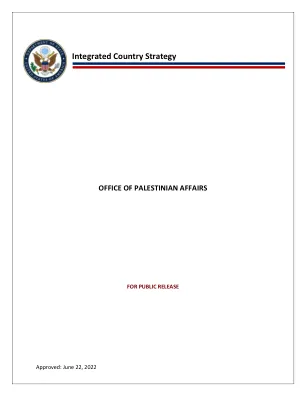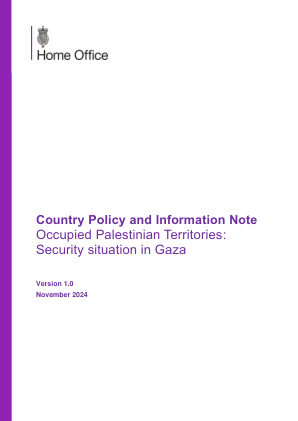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巴勒斯坦教育体系的斗争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研究加沙持续冲突对其教育系统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教育灭绝”。这项研究记录了对包括学校和大学在内的教育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以及针对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定点杀害,这些都阻碍了当前和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本文认为,故意拆除加沙教育机构的目的是抹杀巴勒斯坦人的文化、身份和韧性,从而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任何前景。作者强调,迫切需要国际问责和支持,以重建加沙的教育部门,维护其在社会发展、身份保护和人权方面的作用。设计/方法/方法——本研究论文采用定性设计,使用通过全面审查灰色和学术文献收集的数据来评估持续冲突对加沙教育系统的影响。通过分析财务报告、工作文件和会议摘要,
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分裂经济
雅各布·梅泽尔 (Jacob Metzer) 的书采用了系统但非技术性的方法,是第一本从现代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托管巴勒斯坦分裂经济的书。虽然现有文献通常侧重于犹太经济,但本书探讨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的经济活动。本书借鉴了最近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整个国家建立的国民收入账户,提供了有关巴勒斯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他们的经济表现和双边关系以及该国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等关键主题的新定量证据和解释。这些主题在“二元经济”假设的背景下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将一般“二元”性质的发展差距与特定的民族政治因素区分开来。最后一章回顾了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中阿拉伯-犹太人在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由现在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组成)复杂而不安的经济共存记录。本书有望为现代中东的经济史和对阿以冲突的理解做出重大贡献。新数据的集中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源。
加州理工学院为巴勒斯坦抗议
在上一期的 Tech 杂志中,我们发表了一封大约 150 位教授写给 Rosenbaum 校长的私人信件。这封信不打算与教职员工以外的人分享,信中表达了对应届本科生学业成绩的不满,并主张结束招生办公室的标准化考试禁令。我们发表这封信的目的是确保学生也能参与到这场对话中,因为很明显,如果不这样做,教职员工就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令人遗憾的是,这封信最终成为了他们观点的公开方式;可能各方都会同意,它的写作质量和信息呈现方式都很低劣且无效。同样,这封信是私人通信,不打算发表。然而,当我们在 2 月份联系这封信的五位作者,要求他们提供论点摘要或公开声明时,Tech 杂志却沉默了。 John Dabi-ri 教授和 Paul Asimow 教授慷慨地分享了他们对这封信的看法(见 1 月 16 日和 2 月 6 日的 Tech 杂志),但全文仍然是所有签名者观点的最佳体现。与 Tech 杂志分享这封信的人要求我们不要印刷签名名单或个别教授的附加评论;这个问题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重要,点名批评特定的人会适得其反。当然,这封信提供了电气工程选修课 EE44 和 EE55 的两门必修课的数据。具体来说,它包含了过去两年课程的(匿名)考试成绩和成绩统计数据。回想起来,尤其是考虑到电气工程专业的班级规模很小,我们在没有审查班级姓名或征得所涉学生许可的情况下发布这些内容是不负责任的。我谨代表理工学院公开向这些班级的学生道歉,因为这是他们的错误判断。我很高兴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对这封信做出回应,这封信可以在本期找到。从我与他们的交谈中,听起来我们确实成功地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了有意义的对话,至少在电子工程系是这样。
巴勒斯坦幼儿发展网络...
阿拉伯幼儿发展网络(ANECD)是一个阿拉伯机构,通过与与童年有关的机构提供支持和网络来开发,提高和保护幼儿期,通过产生知识,倡导和影响政策。巴勒斯坦幼儿发展网络(PNECD)来自更广泛的ANECD,并一直在通过开展倡议,鼓励伙伴关系和支持信息交换来提倡并为巴勒斯坦的幼儿发展提供支持。鉴于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必须考虑到不断发展的状况和挑战,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和适应幼儿发展计划。 本报告将重点介绍一些PNECD成员的活动及其在加沙和西岸的工作。鉴于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必须考虑到不断发展的状况和挑战,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和适应幼儿发展计划。本报告将重点介绍一些PNECD成员的活动及其在加沙和西岸的工作。
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统计援助的报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经济的发展
在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被复杂化,并在某些方面被边缘化,这是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由于占领银行在大面积地区的威胁所触发的严重财政危机。在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的长期和加深的职业和对流动性的限制的背景下,这些发展使2020年以来,自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国家权威以来,这使2020年成为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大流行冲击严重程度,但占领仍然是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发展的主要障碍。2021年的经济复苏以及超越铰链对占领力和捐助者支持规模将采取或不会采取的行动。2021年缓慢或不足的恢复将增加大流行带到边缘的中小型企业破产的风险。巴勒斯坦国家权力的负责责任远远超过了所掌握的资源和政策空间。此外,最近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对加沙地带的经济影响以及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其他地区的对抗中预计将是巨大的,联合国应在未来的报告中考虑到。在占领结束之前,无法替代捐助者和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来重建破碎的物理和机构基础设施和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为了转化为真正的进步,应取消占领权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施加的所有限制。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吞并政策(……
与北部被占领城市具有绝对的领土毗连性,从而进一步将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与拉马拉隔离开来。这些三角定居点对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可行的巴勒斯坦首都前景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一旦实施,这些定居点将严重影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社会经济上可行的首都的愿望,同时进入拉马拉、伯利恒、约旦河谷和杰里科的通道也将减少。这些定居点将限制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急需增长的最后可用空间,同时促进非法定居点的建设和扩张,限制传统巴勒斯坦经济中心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此外,它还切断了连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其余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国家交通轴线,使以色列的连续领土最大化,而巴勒斯坦的人口在城市边界内最小化,并在领土上将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分隔开来。如果实施这些三角定居点,巴勒斯坦的连续性和控制将变得不可能,开发区将并入以色列,从而切断巴勒斯坦首都在东耶路撒冷的任何可行性前景。
巴勒斯坦经济:风暴过后仍无平静
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看,由于看不到军事行动停止的迹象,自战争初期以来,美国官员和评论家对巴勒斯坦政权更迭的关注似乎近乎偏执,有时甚至有些妄想。当然,我们都关心加沙及其陷入困境的人民将如何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当然,没有巴勒斯坦人希望回到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政治和地理分歧尖锐且不断扩大的政治现状。我们也不渴望战前以色列定居点加速扩张、土地掠夺和定居者在西岸暴力活动的局面,更不用说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经济崩溃,15 年前,加沙地带的经济规模已经缩减了一半。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加沙安全局势
3.1.4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加沙地带的这场新冲突经常被称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截至本文发表时仍在继续。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以色列国防军 (IDF) 拥有约 170,000 名现役人员和 300,000 至 360,000 名现役预备役人员。其主要对手哈马斯是一个指定的恐怖组织,自 2007 年以来一直实际控制着加沙地带,在冲突之前,其武装派别卡桑旅拥有 15,000 至 40,000 名战士。与哈马斯结盟并积极参与与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的是加沙第二大武装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IJ)。 PIJ 也是指定的恐怖组织,据估计,在冲突开始之前,其武装派别 Al-Quds Brigades 的战士人数约为数百至 15,000 人。消息来源表明,至少有 7 个其他武装团体的数千名巴勒斯坦战士也在积极与以色列国防军作战(见行动者)。
任务报告 - 北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将工作重点放在与技术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上,以及北约为适应当今这些技术的快速发展必须采取的措施上。正是在这一重新聚焦的框架内,来自八个盟国和两个伙伴国家(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十三名议员在德国度过了一周时间,收集了有关未来民用和军事技术的信息以及它们带来的可能性和风险。该代表团由STC技术趋势和安全小组委员会副主席让-克里斯托夫·拉加德(法国)率领。德国驻北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代表团团长卡尔·拉默斯对各位成员来到柏林表示热烈的欢迎。二.德国创新服务研究的主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