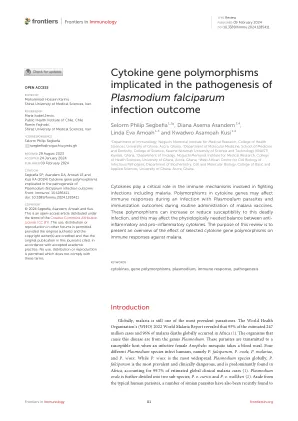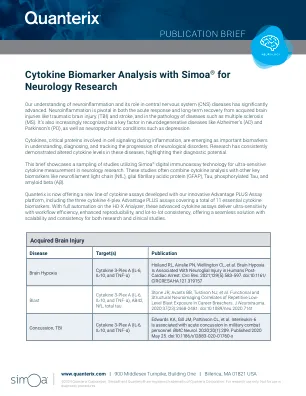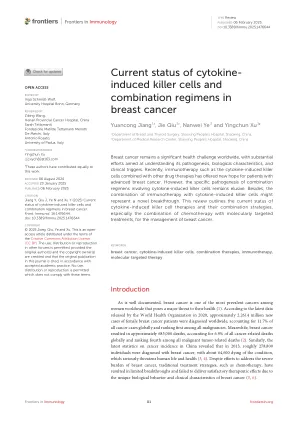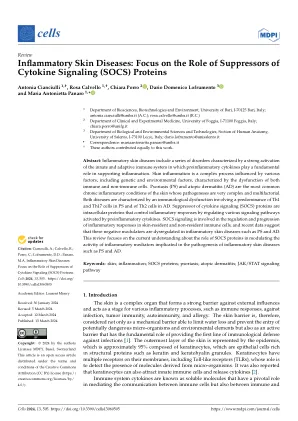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恶性疟原虫感染结果的发病机理
在全球范围内,疟疾仍然是最普遍的寄生虫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全球估计有2.47亿例和96%的疟疾死亡发生在非洲(1)。引起该疾病的生物来自疟原虫属。当感染性雌性蚊子摄取血液餐时,这些寄生虫会传播到易感宿主。四种不同的疟原虫感染了人类,即恶性疟原虫,P。ovale,P。疟疾和Vivax。虽然Vivax是全球最广泛的质量物种,但恶性疟原虫是最普遍,最危险的,并且主要在非洲发现,占估计全球临床疟疾病例的99.7%(1)。卵子疟原虫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种; P.O。柯蒂西和P. Wallikeri(2)。除了典型的人类寄生虫外,最近还发现了许多猿猴寄生虫
免疫细胞因子和PD-1阻滞的免疫疗法增强了抗癌
(未通过同行评审认证)是作者/资助者。保留所有权利。未经许可就不允许重复使用。此预印本版的版权持有人于2020年12月4日发布。 https://doi.org/10.1101/2020.06.03.129049 doi:Biorxiv Preprint
免疫细胞因子和 PD-1 阻断的免疫疗法可增强抗癌效果
本预印本的版权所有者(此版本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发布。;https://doi.org/10.1101/2020.06.03.129049 doi: bioRxiv preprint
使用Simoa®进行神经病学的细胞因子生物标志物分析...
我们对神经炎症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中的作用的理解已显着提高。神经炎症在急性反应和长期康复中都至关重要,例如创伤性脑损伤(TBI)和中风,以及多发性硬化症(MS)等疾病的病理学。它也越来越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氏症(AD)和帕金森氏症(PD)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键因素,以及抑郁症等神经精神疾病。
乳腺癌中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和组合方案的现状
乳腺癌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健康挑战,旨在了解其发病机理,生物学特征和临床触发因素。最近,诸如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以及其他药物疗法的免疫疗法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然而,涉及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的组合方案的特定发病机理仍然难以捉摸。此外,免疫疗法与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的结合可能代表了新的突破。本综述概述了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疗法的当前状态及其结合策略,尤其是化学疗法与分子靶向疗法的组合,用于治疗乳腺癌。
一种遗传的mtDNA突变重塑巨噬细胞和体内炎症细胞因子反应
巨噬细胞中线粒体生物能的受损可能会驱动高炎性细胞因子反应1-6,但是是否也可能是由遗传的mtDNA突变引起的。在这里,我们使用一种多摩变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该方法将超分辨率成像和代谢分析整合到来自丙氨酸7的线粒体trNA中异质质突变(M.5019a> g)的线粒体疾病的小鼠模型中的巨噬细胞。这些M.5019a> G巨噬细胞在呼吸链复合物中表现出缺陷,并且由于中骨内部翻译减少而导致氧化磷酸化(OXPHOS)。以适应这种代谢应激,线粒体融合,还原性谷氨酰胺代谢和有氧糖酵解均增加。在炎症激活后,I型干扰素(IFN-I)释放得到增强,而在M.5019a> G巨噬细胞中限制了促炎性细胞因子和黄磷脂的产生。最后,使用M.5019a> G小鼠的体内内毒素性模型显示IFN-I水平和疾病行为升高。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响应致病性mtDNA突变的先天免疫信号传导的意外失衡,对MTDNA疾病患者的病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
炎症性皮肤疾病:关注细胞因子信号传导(SOCS)蛋白质的作用
摘要:炎症性皮肤疾病包括一系列疾病,其特征是对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强烈激活,其中促炎性细胞因子在支持炎症中起着基本作用。皮肤炎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和环境因素,其特征在于免疫和非免疫细胞的功能障碍。牛皮癣(PS)和特应性皮炎(AD)是皮肤中最常见的慢性炎症状况,其病原体非常复杂且多因素。两种疾病的特征是免疫功能障碍,涉及AD中PS和Th2细胞中Th1和Th17细胞的占主导地位。抑制细胞因子信号传导(SOCS)蛋白是细胞内蛋白,通过调节促炎细胞因子激活的各种信号通路来控制炎症反应。SOCS信号传导参与皮肤和非居民免疫细胞中炎症反应的调节和进展,最近的数据表明,这些负调节剂在PS和AD等炎症性皮肤疾病中失调。本综述着重于当前对SOC蛋白在调节炎症性皮肤疾病(如PS和AD)发病机理的炎症介质活性中的作用的理解。
小胶质细胞因子介导 10 Hz 重复磁刺激引起的可塑性
1 弗莱堡大学医学院解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神经解剖学系,79104 弗莱堡,德国,2 弗莱堡大学 Spemann 生物医学研究生院,79104 弗莱堡,德国,3 弗莱堡大学生物学院,79104 弗莱堡,德国,4 弗莱堡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研究所,79106 弗莱堡,德国,5 弗莱堡大学药学研究所药物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系,79104 弗莱堡,德国,6 弗莱堡大学医学院医学中心血液学、肿瘤学和干细胞移植系,79106 弗莱堡,德国,7 九州大学药学研究生院分子与系统药理学系,福冈,812-8582,日本,8弗莱堡大学信号研究中心 BIOSS 和 CIBSS,79104 弗莱堡,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院神经调节基础中心 (NeuroModulBasics) 9,79106 弗莱堡,德国,弗莱堡大学 BrainLinks-BrainTools 中心 10,79110 弗莱堡,德国
IL-6 细胞因子家族中具有更多多效性 - -ORCA
另一层调节。早期对 OSM 信号的研究提供了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例子。人类 OSM 可以通过由 OSMR 或 LIFR 组成的 gp130 受体盒发出信号,当通过 LIFR 发出信号时,OSM 可以控制通常与 LIF 相关的活动(例如造血、全能性)。同样,CNTF 与 IL-6R 的结合亲和力较低,可能通过由 IL-6R 和 LIFR 组成的 gp130 受体盒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引发类似 IL-6 的活动(图 2)。思考为什么存在这些共同的关系很重要。这些相互作用是否会导致信号传导潜力的差异,如研究描述 IL-11 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ERK/MAPK) 信号所示,据称这比报道的 IL-6 更为突出 [8]。根据 Weitz 等人的数据,Il6ra/小鼠在伤口愈合过程中表现出增强的 ERK/MAPK 信号传导 [9] 。如果 IL-6 信号传导和 IL-11 信号传导确实不同,那么当 IL-6 通过 IL-11R 起作用时,从分子上定义信号转导途径将会很有趣。
免疫学角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当今每个医生必须知道什么?
“细胞因子风暴”这一术语最早于 1993 年由 Ferrara 等人使用,用于描述移植中的移植物抗宿主病。1 随后,细胞因子风暴被认为与严重病毒感染、自身免疫和血液病以及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关。随着当前冠状病毒病-2019 (COVID-19) 大流行,不仅医学界而且普通公众对这一现象重新产生了兴趣。尽管已经发表了多篇关于细胞因子风暴及其与当前大流行的相关性的论文,但必须注意的是,对于什么是“细胞因子风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尽管我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越来越多,但针对风暴进行免疫调节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本文将概述“细胞因子风暴”并以简化的方式描述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