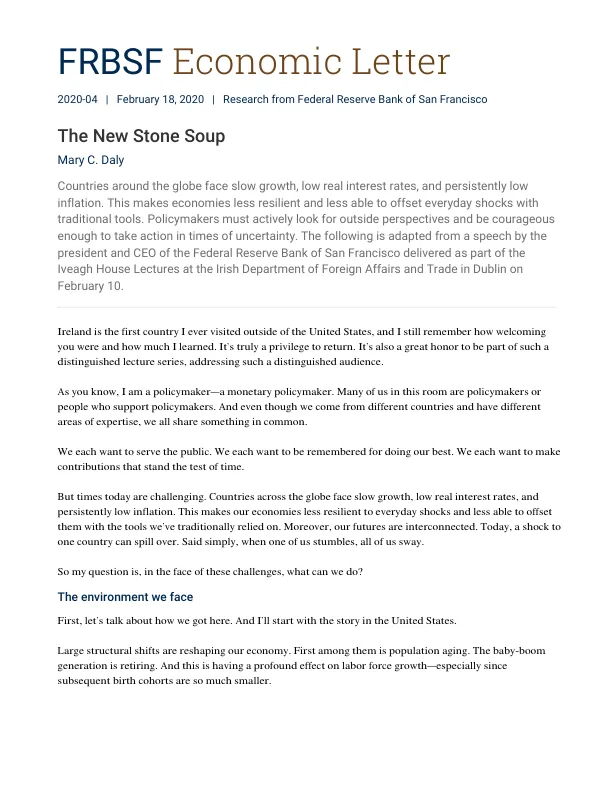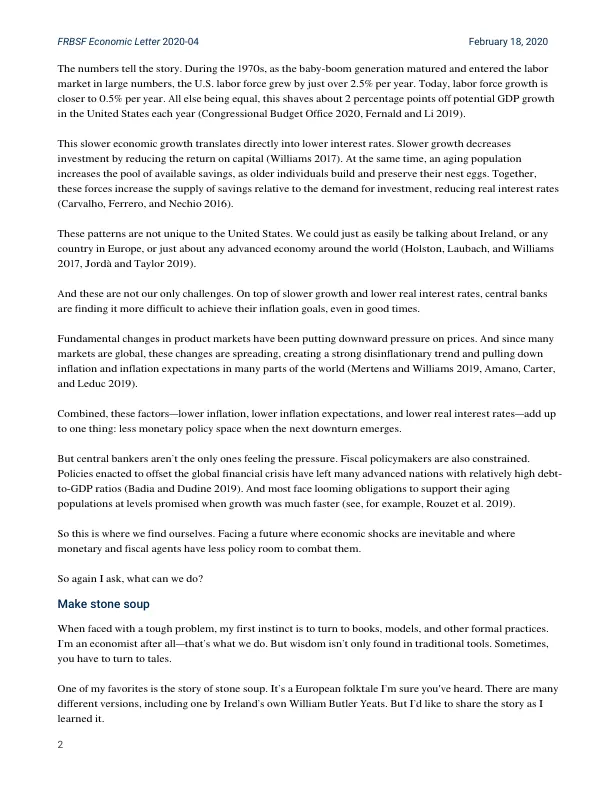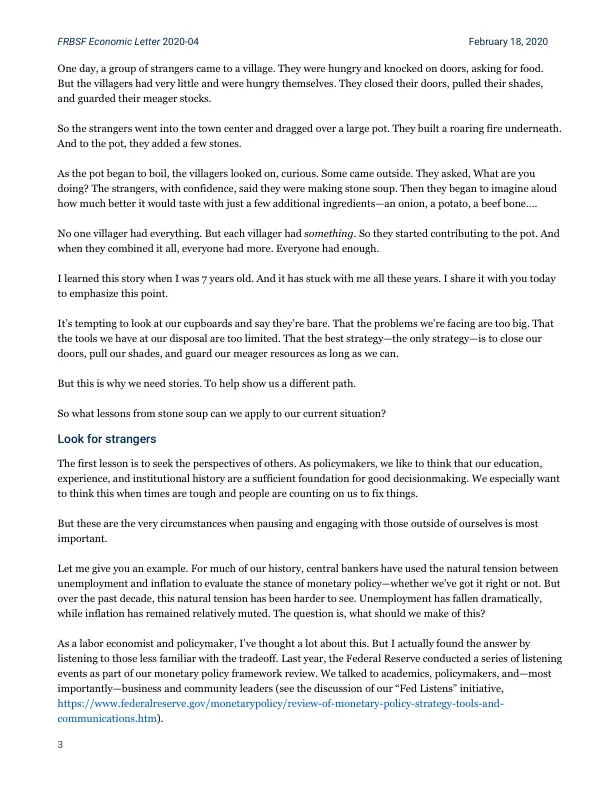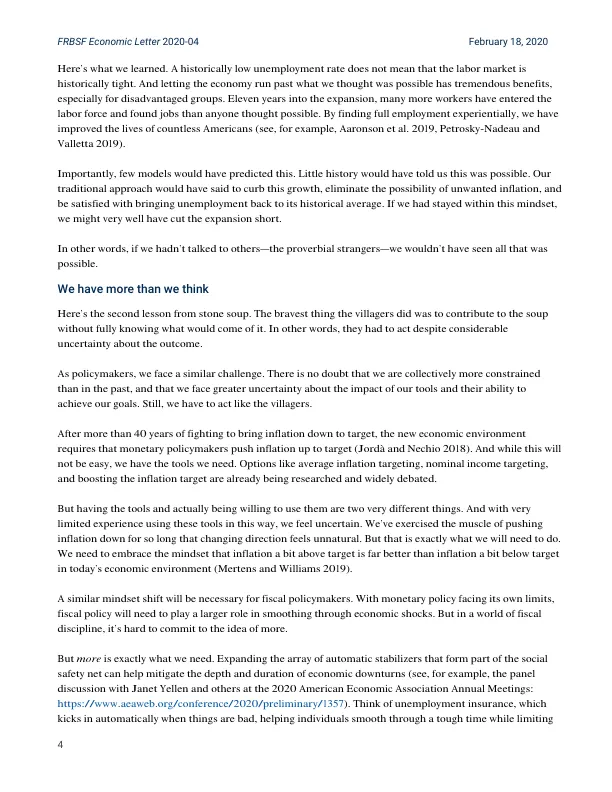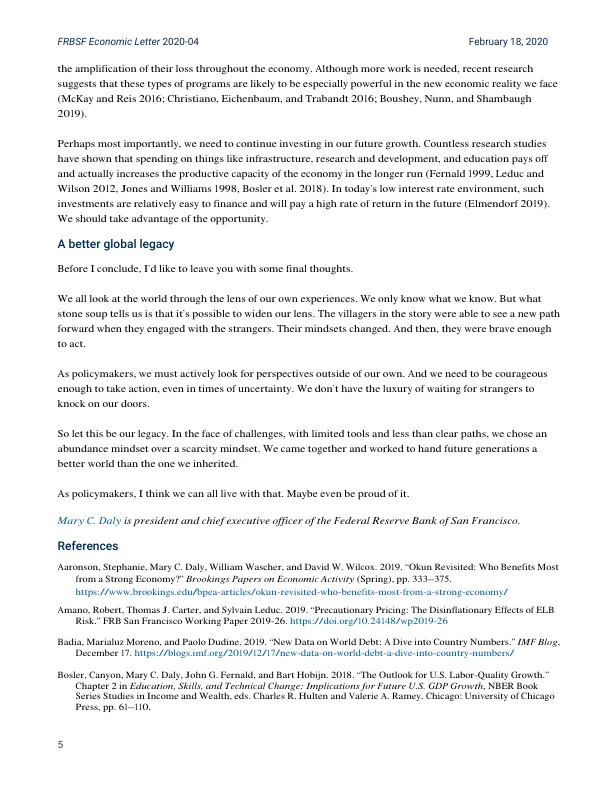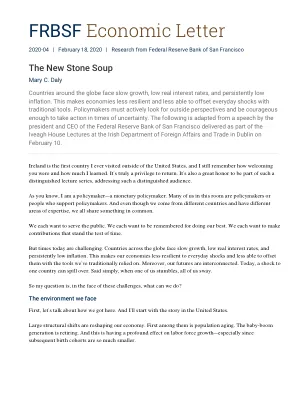数字说明了一切。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熟并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力每年增长略高于 2.5%。如今,劳动力增长率接近每年 0.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每年会降低美国潜在 GDP 增长率约 2 个百分点(国会预算办公室 2020 年,Fernald 和 Li 2019 年)。经济增长放缓直接导致利率下降。增长放缓会通过降低资本回报率来减少投资(Williams 2017 年)。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可用储蓄池,因为老年人会积累和保留他们的储蓄。这些力量共同增加了储蓄相对于投资需求的供应,从而降低了实际利率(Carvalho、Ferrero 和 Nechio 2016 年)。这些模式并非美国独有。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谈论爱尔兰,或欧洲的任何国家,或世界上几乎任何发达经济体(Holston、Laubach 和 Williams 2017,Jordà 和 Taylor 2019)。而这些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挑战。除了增长放缓和实际利率下降之外,央行发现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实现通胀目标也变得更加困难。产品市场的根本性变化给价格带来了下行压力。由于许多市场都是全球性的,这些变化正在蔓延,形成强大的通货紧缩趋势,拉低了世界许多地区的通胀和通胀预期(Mertens 和 Williams 2019,Amano、Carter 和 Leduc 2019)。这些因素——通胀率下降、通胀预期下降和实际利率下降——加在一起就是一件事:下一次经济衰退出现时,货币政策空间将减少。但央行行长并不是唯一感受到压力的人。财政政策制定者也受到制约。为抵消全球金融危机而制定的政策导致许多发达国家的债务与 GDP 比率相对较高(Badia 和 Dudine,2019 年)。而且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义务,即以经济增长更快时承诺的水平来支持老龄化人口(例如,参见 Rouzet 等人,2019 年)。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面对未来,经济冲击不可避免,货币和财政机构应对这些冲击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再次问,我们能做什么?
新石头汤
主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