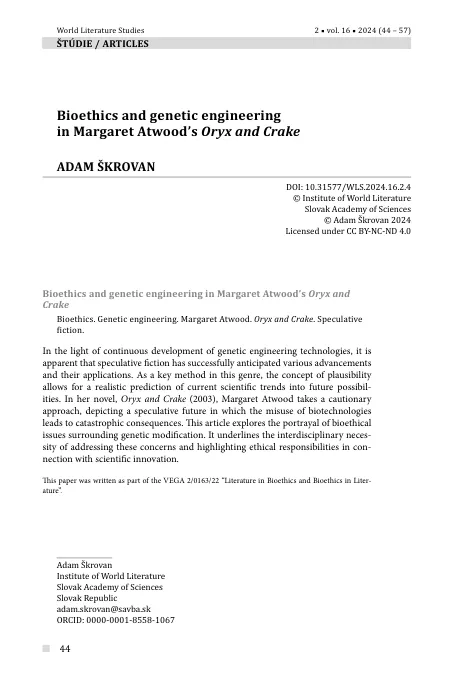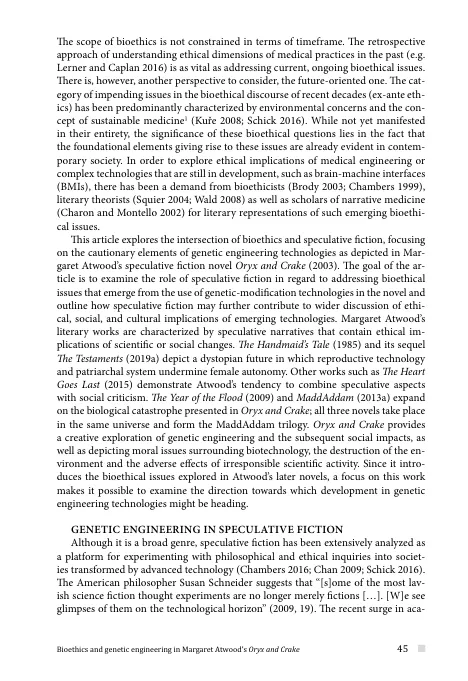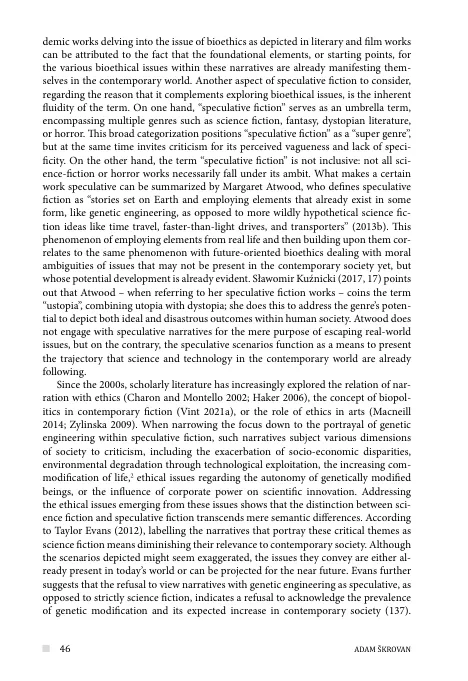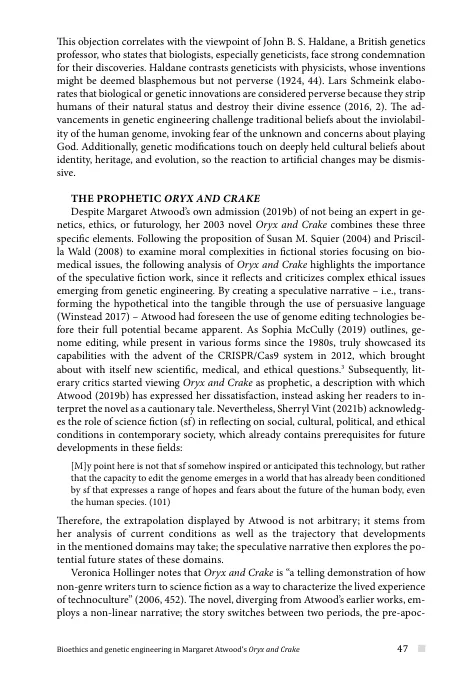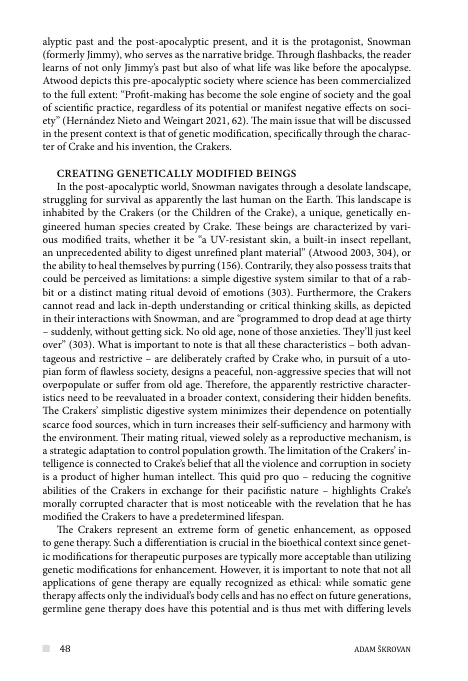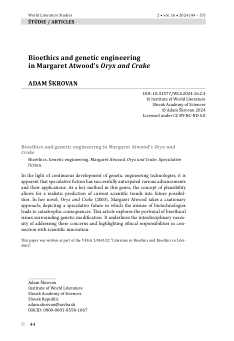生物伦理学的范围不受时间框架的限制。回顾性地理解过去医疗实践的伦理层面(例如 Lerner 和 Caplan 2016)与解决当前正在发生的生命伦理问题同样重要。然而,还有另一个角度需要考虑,即面向未来的角度。近几十年来生物伦理话语中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类别(事前伦理)主要以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医学 1 的概念为特征(Kuře 2008;Schick 2016)。虽然这些生物伦理问题尚未完全体现出来,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引发这些问题的基础要素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很明显。为了探索医学工程或仍在开发中的复杂技术(如脑机接口 (BMI))的伦理影响,生物伦理学家 (Brody 2003;Chambers 1999)、文学理论家 (Squier 2004;Wald 2008) 以及叙事医学学者 (Charon and Montello 2002) 都要求对此类新兴生物伦理问题进行文学描述。本文探讨了生物伦理学与推想小说的交集,重点关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推想小说《羚羊与秧鸡》(2003) 中描绘的基因工程技术的警示元素。本文旨在研究推想小说在解决小说中使用基因改造技术所带来的生物伦理问题方面的作用,并概述推想小说如何进一步促进对新兴技术的伦理、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更广泛讨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作品以思辨性叙事为特点,其中包含科学或社会变革的伦理含义。《使女的故事》(1985)及其续集《遗嘱》(2019a)描绘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生殖技术和父权制破坏了女性自主权。其他作品如《心在最后》(2015)表明阿特伍德倾向于将思辨性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洪水之年》(2009)和《疯狂亚当》(2013a)扩展了《羚羊与秧鸡》中呈现的生物灾难;这三部小说都发生在同一个宇宙中,构成了疯狂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创造性地探索了基因工程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并描绘了围绕生物技术的道德问题、环境破坏和不负责任的科学活动的不利影响。由于它介绍了阿特伍德后期小说中探讨的生物伦理问题,因此关注这部作品可以让我们了解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中的生物伦理学和基因工程
主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