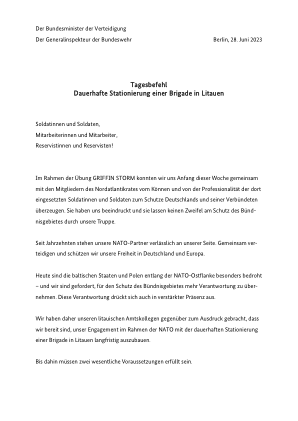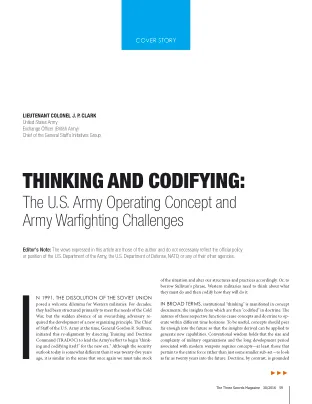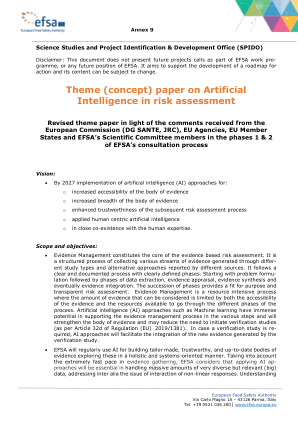机构名称:
¥ 1.0
“ 劣势生育 ” 的概念源于优生学思想,由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在 19 世纪推广 [1,2]。高尔顿和其他优生学家认为,人类种群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得到“改良”;鼓励具有“理想”特征的人生育孩子,同时阻止具有“不良”特征的人生育孩子。通过选择性育种来“改良”人类种群被称为“优生学”。“ 劣势生育 ” 是优生学的反义词,指通过“不良”特征的增殖而导致人口“退化”。因此,优生学家使用“ 劣势生育 ” 这一短语来表示具有“不良”特征的人比具有“理想”特征的人生育更多孩子。他们认为,这将导致那些“不良”特征在人群中被选择,并因此变得更加普遍。自从高尔顿首次创造优生学一词以来,优生学家的普遍信念是,较高的认知能力或“智力”是一种“理想”特征,是天生优越者的标志。因此,认知能力和生育能力之间的负相关是“不良生育”的一个例子。许多优生学家利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人类群体中认知能力与生育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的说法来为他们喜欢的社会政策辩护,比如减少社会福利。在优生学家的信仰体系中,社会福利通常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鼓励“不良人群”生育 [3-6]。 Bratsberg & Rogeberg [7] 的论文研究结果实际上挑战了优生学家的主张,优生学家认为认知能力与生育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他们发现挪威男性的认知能力与生育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还提供了证据,反驳了优生学家的典型主张,即“社会福利政策提高了低能力父母的相对生育能力”。然而,Bratsberg & Rogeberg 在他们的论文中毫无批判地采用了优生学家的劣生框架:他们只是得出结论
“不良生育”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科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