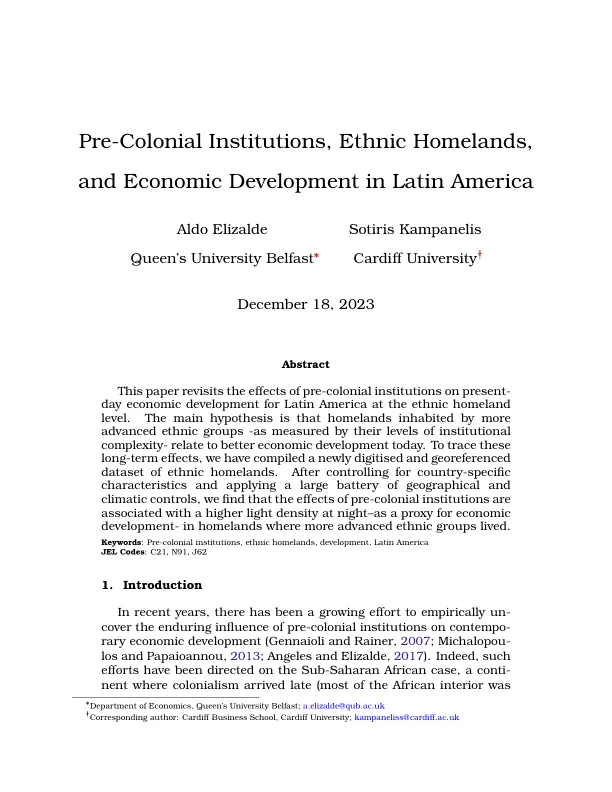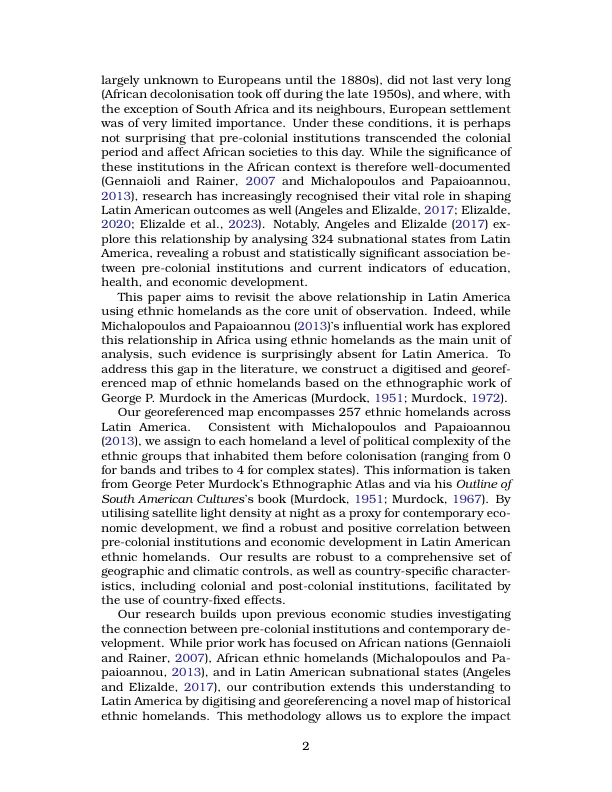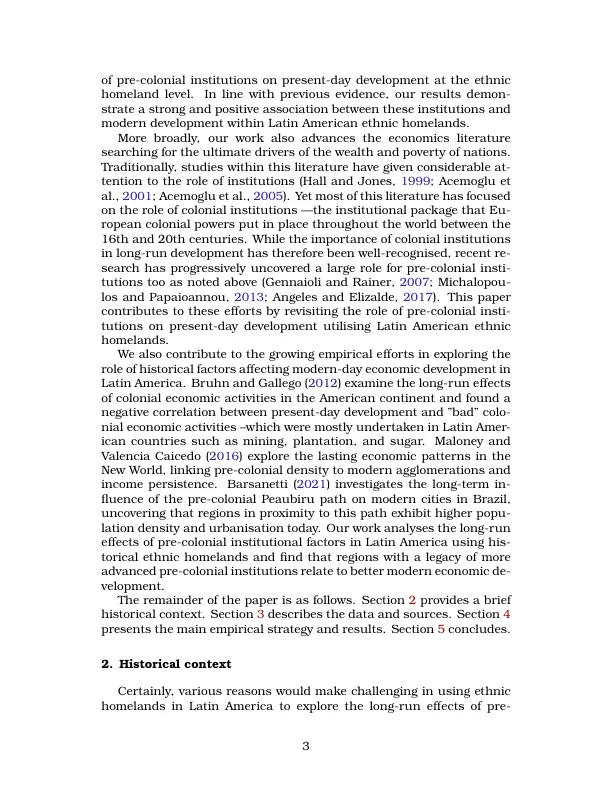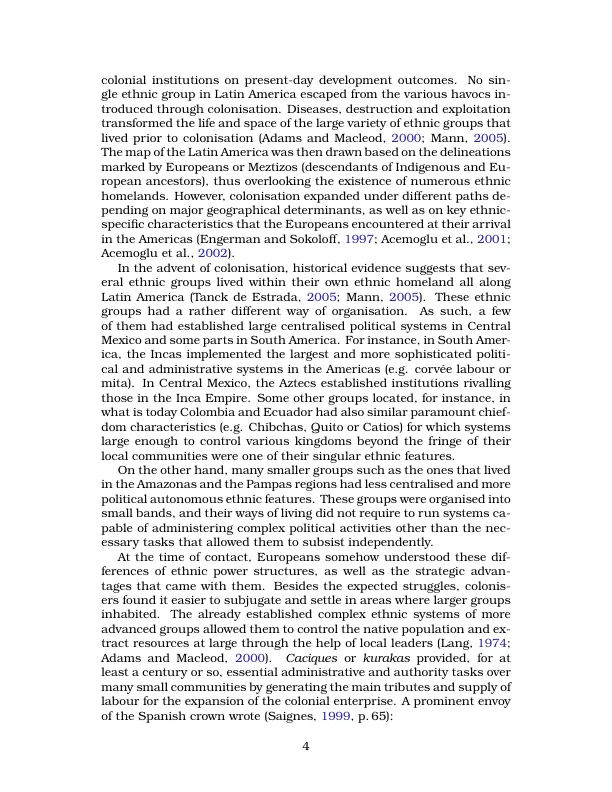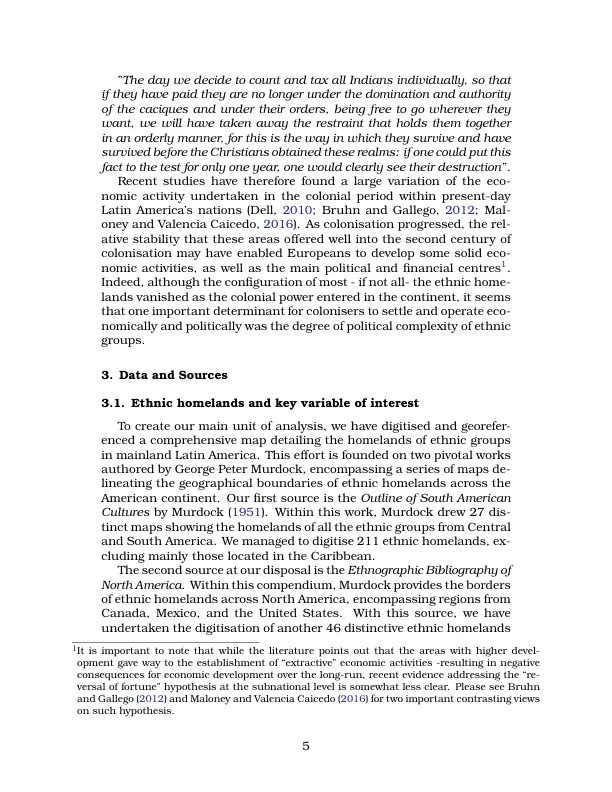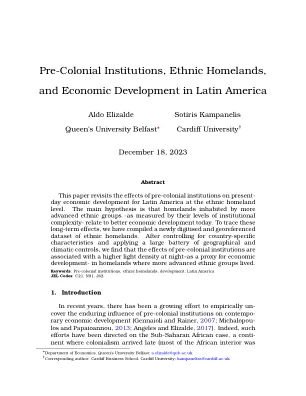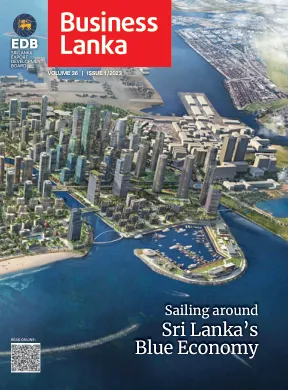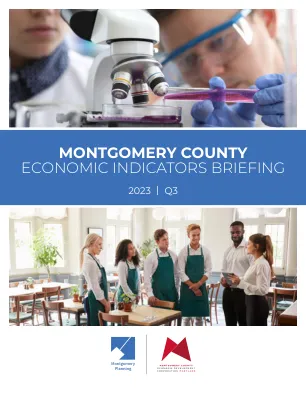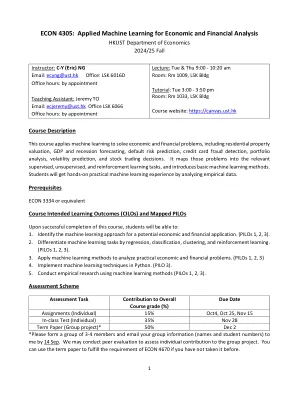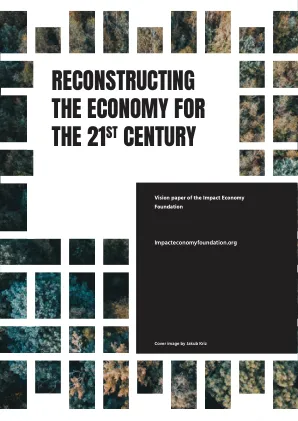直到1880年代,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不知道),持续很长时间(非洲非殖民化在1950年代后期起飞),除南非及其邻国外,欧洲定居点的重要性非常有限。在这些条件下,前殖民机构超越了殖民时期并影响到今天的非洲社会也许并不奇怪。因此,这些机构在非洲背景下的重要性是有据可查的(Gennaioli和Rainer,2007年,以及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年),研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们在塑造拉丁美洲成果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Angeles and Elizalde,2017; Elizalde; Elizalde; Elizalde; Elizalde; 2020; Elizald; elizalde and and and 202,23。值得注意的是,Angeles and Elizalde(2017)通过分析拉丁美洲的324个次国家国家来表达这种关系,从而揭示了殖民前机构以及当前教育,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当前机构以及当前的指标。本文旨在使用种族祖国作为观察的核心单位来重新审视拉丁美洲的上述关系。的确,尽管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的有影响力的工作探索了在非洲的这种关系,但族裔家乡作为分析的主要单位,但对于拉丁美洲而言,这种证据令人惊讶。为了解决文献中的这一差距,我们根据乔治·P·默多克(George P. Murdock)在美洲的民族志工作建造了数字化和地理标志的种族祖国地图(Murdock,1951; Murdock; Murdock,1972)。我们的地图涵盖了拉丁美洲的257个种族家园。与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年)一致,我们为每个家园分配了在殖民之前居住的种族群体的政治复杂性(从乐队和部落的0到4的4)。此信息摘自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的民族志地图集,并通过他的南美文化著作(Murdock,1951; Murdock,1967)的概述。通过在夜间利用卫星光密度作为当代生态发展的代理,我们发现了殖民前机构与拉丁美洲族裔家园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牢固而积极的相关性。我们的结果对于一组全面的地理和气候控制以及特定国家特定的特征,包括殖民地和后殖民机构,这是通过使用乡村固定效应来促进的。我们的研究基于以前的经济研究,研究了殖民机构与当代诉讼之间的联系。虽然先前的工作集中在非洲国家(Gennaioli和Rainer,2007年),非洲种族家园(Michalopoulos和Paioannou,2013年)和拉丁美洲亚美国国家国家(Angemes and Elizalde,2017年),我们的贡献扩展了这一对拉丁美洲的理解,通过数字化和地图为拉丁美洲,通过数字化和地图为历史悠久的历史上的历史悠久的历史文献。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探索影响
前殖民机构,种族家园和经济...
主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