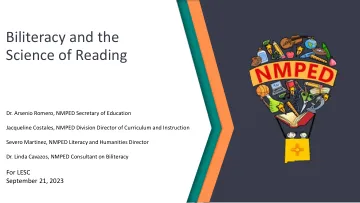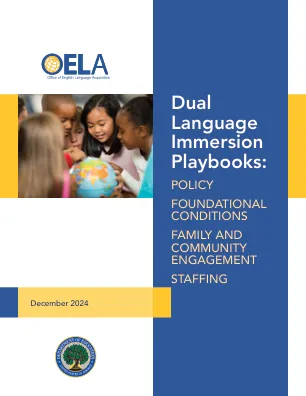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测量双语
摘要双语的研究具有从解密的古代多语言文本到映射多语言大脑的结构的历史。独立双语者的语言体验同样多样化,其特征是独特的获取和使用背景,不仅可以塑造社会文化认同,而且可以塑造认知和神经功能。也许毫不奇怪,学术观点和语言经验中的这种可变性已经引起了定义双语主义的一系列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发起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学习和衡量双语主义的更统一方法的对话。使用具体的案例研究,我们说明了在问题,域内不同的问题和科学询问中不同方法中使用不同方法的研究人员增强沟通和简化术语的价值。我们特别考虑双语商(BQ)构造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讨论相对于已建立良好的智能商的BQ的想法,并包括下一步的建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语言背景的变异性和定义双语的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但在整个领域进行系统化和综合研究的协同努力可能会构建有效且可推广的多语言经验索引。
双语对认知加工的影响
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在双语能力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方面存在语境和方法论上的差距。初步实证研究表明,双语能力与认知优势相关,例如增强的注意力控制、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容量。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双语者在认知任务中的表现通常优于单语者,这支持了双语优势理论。此外,有证据表明,双语能力可能有助于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的衰退速度。这些发现对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具有重要意义,凸显了推广双语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的潜在益处。
双语沉浸式教学手册: - NCELA
DLI 项目 为了解更多有前景的和其他基于证据的 DLI 实践和项目,美国教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收集了来自 WestEd 和第 2、6、14 和 15 区综合中心以及五个 SEA(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的信息。之所以选择这些州,是因为它们的 DLI 项目数量最多,每个州都有 200 多个 DLI 项目。12 DLI 项目首先从文献扫描开始,用于创建一系列考虑因素和指导问题,以确定可以实现高质量和包容性的 DLI 项目的政策、流程、项目和实践。13 每个 SEA 都围绕关键问题和考虑因素,确定了要访问的“亮点”——拥有高质量研究型项目、学生出勤率高和家长参与度高的公立学校。在选择 DLI 亮点时,SEA 被鼓励考虑人员配备、专业发展、项目愿景和目标、课程和评估、教学技术、学生构成、增加 EL 访问权限的过程、项目实施政策、SEA 和 LEA 级别政策以及学生成果。
双语处理和获取 - 简介
如何发展对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的知识,以及在实时理解和一种或两种语言中使用的知识如何?双语开发和处理是本书探索的中心主题,最初是根据第一语言(S)(L1)而探讨的,然后是其他语言。人类的生长和发展必然涉及时间的流逝,刺激了这种正交因素,并导致观察到能力在整个寿命中可能会有所不同。两个理论框架在历史上已经归因于知识和使用语言,自然与养育方法的解释(Galton 1876):前者归功于生物遗传的内在特征,而后者则将环境外在经验归因于发展变化的原因。te证据将导致更加细微,更复杂的观点,避开二分法,并赞成考虑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影响的混合方法。的确,“没有两者都不会发生发展,并且由于自然而改变了自然而自然的变化”(Shulman 2016,75;另请参见Resende 2019)。双语者表明,根据何时以及如何获取两种语言的方式(语言获取,洛杉矶;有关儿童洛杉矶的讨论),请参见De Houwer 2021。te术语的开发,获取和学习通常在本书中互换使用,并包括“指导和非实施者,无论是隐式和明确的》(de Houwer&Ortega 2019b,2,2)。第一个审查是同时学习两种语言(2l1a)的双语者,并且可以称为婴儿床双语者。从两种语言中获得大量意见并在两种语言中都具有稳固培训的教育机会的可比访问权限的孩子都认为平衡能力。但是,双语的两种语言永远不会完全平等或平衡(de Houwer 2018a,b; Grosjean 2008),因此该术语(尽管广泛使用)并不是真正准确的。第二个要研究的是幼儿,他们从三到六岁的年龄获得第二语言(CL2A)掌握其L1的核心特征;这样的个体被描述为早期顺序
双模双语:关键在于...... - PsyLing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了解人类神经认知发展如何受到社会和语言经验的影响。聋哑父母的听力正常儿童(也称为 CODA)是一个有趣的群体,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交流经验,因此可以研究依赖经验的可塑性。事实上,他们可能同时接触手语(例如美国手语)和口语(例如英语),从而导致出现一种特殊的多语言现象:双模态双语现象。尽管传统上关于这一群体的数据有限且往往不一致,但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有语言学习困难的风险。本演讲将讨论最近的数据,比较从婴儿期到学龄期的双模态双语者的大脑激活模式和语言习得概况,并与从出生开始学习两种口语的儿童(单模态双语者)和学习单一语言的儿童(单语者)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语言经验会影响生命最初几个月的大脑语言网络的发展。他们还指出,双模态双语者从婴儿期到学龄期都能成功习得语言,与听力正常的父母的孩子相比,他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以双模态双语为例,本演讲将说明语言专长的形成是一个依赖于儿童环境和经验的适应性过程。
跨发展的双语和创造力-Serval
简介:大量研究证明了双语的创造力。不同的思维和融合思维被认为是创造力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研究(尽管不是全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双语儿童的表现优于不同思维中的单语儿童,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对儿童或青少年的研究,探讨了双语和融合思维之间的关系,或者探索了双语和创造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大脑结构基础。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双语主义对基于神经心理学评估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收敛性和分歧思维的影响,以及通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区域灰质体积(RGMV)和皮质厚度的整个区域灰质体积(RGMV)的全脑分析对双语对创造力的影响的可能性基础。
早期儿童双语:对大脑结构和
摘要 在双语环境中长大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我们对这种丰富的语言环境如何影响儿童大脑的连接知之甚少。儿童和成人的行为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可能会提高执行控制 (EC) 技能,例如抑制控制和注意力。此外,语言相关和 EC 相关大脑网络的结构和功能 (静息状态) 连接增强与双语成人的执行控制增强有关。然而,双语因素如何在大脑发育早期改变大脑连接仍不清楚。我们将结合双语儿童的标准化注意力测试和结构和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MRI)。这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究以下问题来解决语言学和发展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双语经验是否会调节儿童语言相关和 EC 相关网络的连接?静息状态大脑连接的差异是否与 EC 技能(特别是注意力技能)的差异相关?双语相关因素(如接触两种语言的年龄、语言使用和熟练程度)如何影响大脑连接?我们将从两组英语-希腊语双语儿童(20 名同时双语儿童(从出生开始接触两种语言)和 20 名连续双语儿童(3 至 5 岁之间接触英语)和 20 名 8-10 岁的英语单语儿童)收集结构和功能 MRI 以及 EC 和语言技能的定量测量。我们将比较单语者和双语者之间的连接测量和注意力技能,以检查双语接触的影响。我们还将研究双语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预测 EC 和语言网络中的大脑连接。总体而言,我们假设连接和 EC 将在
双语课程内容和语言分配计划
• 熟悉双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让双语教师参与教育目标的制定和实施,• 促进双语教师和主流教师之间的合作,• 聘请来自学生文化的双语员工,• 鼓励双语学生家长的参与,• 支持所有员工参与以新兴双语为重点的专业发展
跑步头:双语和工作记忆1标题
1心理学学校,渥太华大学,渥太华大学,安大略省,K1N 6N5,加拿大2,2认知神经科学单位,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QC H3A 2B4,加拿大3,加拿大3,麦克吉尔大学,麦克吉尔大学,麦克吉尔大学,QC H3G 2A8,CANCACANIDER,MCGILL UNIXIACA蒙特利尔,QC H3A 1G1,加拿大5心理学系/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康科迪亚大学,蒙特利尔,QC H4B 1R6,加拿大6 Bloomfield老龄化研究中心,戴维斯戴维斯夫人医学研究所和犹太犹太人总医院/麦克吉尔大学/麦吉尔大学记忆诊所,Montreal,QC H3T 1E Serkity QC H3T 1E Serkity,Q. 1G1,加拿大8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神经和神经外科系,蒙特利尔,QC H3A 2B4,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