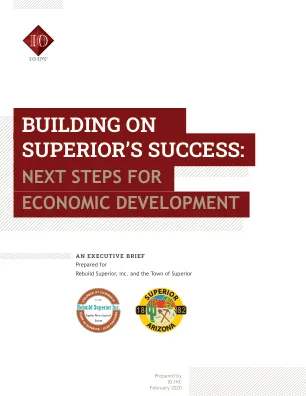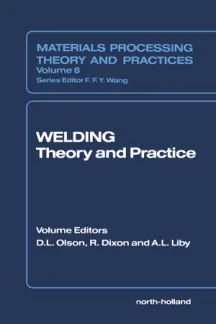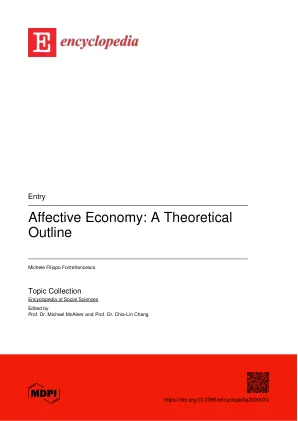《国富论》中讨论了城镇发展以及早期文明和晚期殖民地的发展。斯密使用的所有例子都是他所谓的理论模型的例外,如果斯密真的想用该模型解释发展,那么这个选择就很奇怪了。我不会像 Walter Eltis (1975) 和 Samuel Hollander (1973) 对增长模型那样对斯密的模型进行形式化,而是坚持斯密的叙述。我不会参与有关斯密的唯物主义(Pascal 1938;Meek 1976;Skinner 1982)或缺乏唯物主义(Winch 1983a;Haakonssen 1981)的争论,John Salter(1992)对此进行了评论,但我会研究斯密对发展阶段模型的运用以及他使用的例子。虽然我同意 Hla Myint ( 1977 ) 的观点,即史密斯有“贸易兼发展”理论,但我与 Myint ( 1958 ) 的观点不同,他用实际经验事实来审视史密斯模型的有效性。我只关注史密斯本人提供的经验数据,而不是他的历史发展叙述是否正确。此外,我同意 Paul Bowles ( 1986 ) 的观点,即理论与事实脱节是一个问题,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即这是史密斯的失败,因为重农学派对他产生了影响。如果斯密未能证明“‘富裕的自然进程’描述了经济体在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的发展方式,并且他的失败……源于他的方法论,尤其是‘富裕的自然进程’是一个先验概念,没有参考历史证据” (Bowles 1986,第 110 页),那么斯密为何要费心不断列举与他的模型相矛盾的历史证据?因此,我提出一个问题,即斯密本人是否质疑阶段模型作为发展模型的用途。我认为,发展阶段模型的特殊形式意味着“社会根据不同的生存方式经历连续的阶段发展” (Meek 1976,第 6 页;重点为原文)。因此,这一阶段模型的关键不仅在于生存方式决定了社会的阶段,还在于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社会在进步,即使不同的生存方式可能同时共存。这是罗纳德·米克的解释的关键方面——“发展应被视为经历四个通常连续的阶段”(Meek 1971,第 10 页)——在我看来,斯密要么没有采纳这一解释,要么如果被解释为采纳,我认为斯密是在批评而不是支持。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詹姆斯·阿尔维(James Alvey,2003)的观点,即对斯密的目的论解释是有问题的。我与阿尔维不同,因为我不认为“斯密感到困惑”(Alvey 2003,第 19 页)。正如我认为的,斯密要么没有把阶段性发展模型当作发展模型来采用,要么,如果他采用了,也是在批评它,而不是在认可它。事实上,我对米克及其同类的解读有异议,这些解读认为,正如米克所说,“起初全世界都是美国……美国……是亚洲和欧洲最初时代的一种模式” (约翰·洛克,引自米克,1976 年,第 22 页)——发展阶段的观念意味着或多或少“不同生存方式的有序序列或连续性,通过这种序列或连续性,社会可以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 (米克,1976 年,第 23 页),即使不同的社会可能同时处于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在斯密的理论中看到发展。在斯密的理论中,发展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斯密解释这一历史事实的方式并不是通过“不同生存方式的有序序列或连续”的阶段模型。这并不意味着斯密不考虑不同的阶段
亚当·斯密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主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