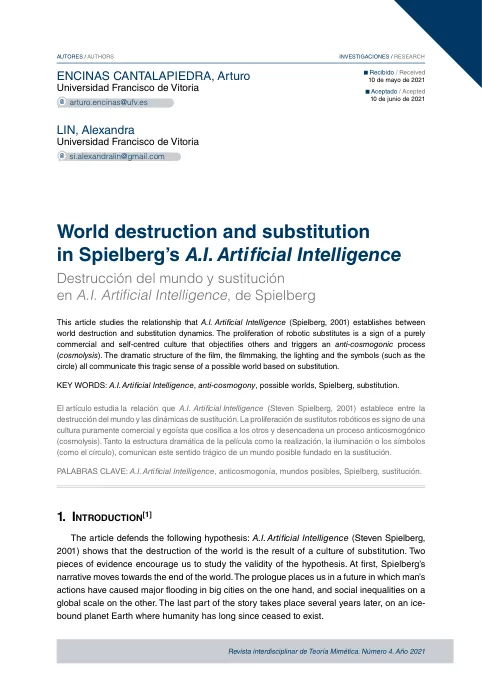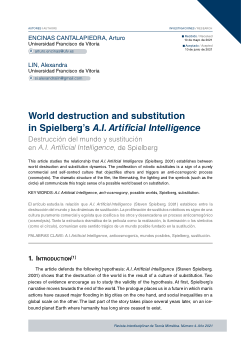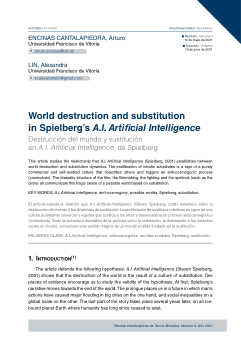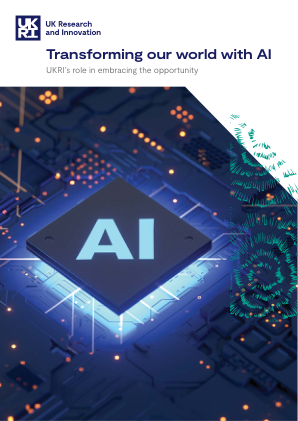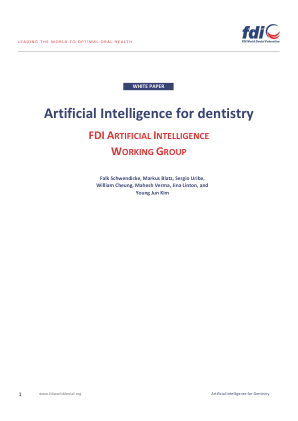支持这一假设的第二个证据是整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替代动态,其模式如下:机器人代替人类担任特定角色;机器人周围的人类将一些错误归咎于替代者;机器人被视为对人类群体遭受的某些不幸负有责任,于是开始淘汰机器人。主线剧情和次要剧情都是由替代引发的,其结果迟早会以悲剧收场 [2] 。主要情节(以替代为标志)本身并不适合用叙事因果关系来解释故事开始和结束之间星球状态的变化。然而,我们认为,在主题层面上,这些替代机制综合了导致世界毁灭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电影中指向这种关系的元素数量多得惊人。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使用了一种包含多个视角的方法:可能世界的解释学、勒内·吉拉尔的模仿理论和视听分析。“很抱歉,我没有告诉你这个世界。”这是莫妮卡·斯文顿在把大卫遗弃在森林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从那一刻起,机器人孩子周围的现实从温暖的家转变为残酷存在的敌意。莫妮卡提到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它还表明了一个人体验现实的方式。世界是一个可能性系统。从广义上讲,这就是我们和莫妮卡所说的“世界”。体验具体事物的方式总是人类体验为世界,而不仅仅是物理世界或生物媒介(Zubiri 2010,第 166-201 页)。因此,当诺博士将大卫送往“狮子哭泣的世界尽头”——他的朝圣目的地时,可以理解的是,主角也正朝着边缘前进,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边缘,而且是存在空间的边缘,在那里他将遇到他的创造者霍比教授。这种世界观由祖比里、瓜尔迪尼(2014 年,第 15-43、70-82 页)或马林(2019 年,第 461-465 页)等人发展,我们在加西亚-诺布莱哈斯(2005 年,第 180、206-207、212 页)关于可能的诗意世界的理论提议中找到了它。帕维尔(1986 年)和埃科(1994 年,第 64-82 页)的文本中也有部分类似的方法。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从人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理解虚构的世界:其中涉及的既不是外延验证(García Noblejas,2005,第 180 页),也不是逻辑命题(Pavel,1986,第 136 页;Eco,1993,第 176-178 页)。它不是关于自然主义意义上的物质宇宙距离的评估,而是它令人着迷地提供了关于意义的生活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塑造个人身份的贡献(García Noblejas,2005,第 17 页)。如果我们接受人工智能的叙事目的。由于人类行为(从伦理维度评估)而走向世界毁灭(在人类学而非宇宙学意义上),那么采用可能世界的视角似乎是合适的,因为它对斯皮尔伯格似乎暗示的世界意义很敏感。为了阐明人工智能中的世界形象,必须研究主要行动冲突中包含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中替代和替罪羊尤其突出。勒内·吉拉德的理论非常清楚这些问题(Girard,1989;2010;2012)。我们不会仅仅从模仿理论的角度分析斯皮尔伯格的作品,
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中的世界毁灭与替代
主要关键词